《路边野餐》里的八首诗
壹
背着手
在亚热带的酒馆
门前吹风
晚了就坐下
看柔和的闪电
背着城市
亚热带季风的河岸
淹没还不醉的桥
不醉的建筑
用静默解酒
明天 阴
摄氏三到十二度
修雨刷片 带伞
在戒酒的意识里
徒然下车
走路到天晴
照旧打开
身体的衣柜
水分子穿越纤维
贰
没有了音乐就退化耳朵
没有了戒律就灭掉烛火
像回到 误解照相术的年代
你摄取我的灵魂
没有了剃刀就封锁语言
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
叁
山
是山的影子
狗
懒得进化
夏天
人的酶很固执
灵魂的酶像荷花
肆
许多夜晚重叠
悄然形成黑暗
玫瑰吸收光芒
大地按捺清香
为了寻找你
我搬进鸟的眼睛
经常盯着路过的风
伍
命运布光的手
为我支起了四十二架风车
源源不断的自然
宇宙来自于平衡
附近的星球来自于回声
沼泽来自于地面的失眠
褶皱来自于海
冰来自于酒
通往岁月楼层的应急灯
通往我写诗的石缝
一定有人离开了会回来
腾空的竹篮装满爱
一定有某种破碎像泥土
某个谷底像手一样摊开
陆
今天的太阳
像瘫痪的卡车
沉重地运走 整个下午
白醋 春梦 野柚子
把回忆揣进手掌的血管里
手电的光透过掌背
仿佛看见跌入云端的海豚
柒
所有的转折隐藏在密集的鸟群中
天空与海洋都无法察觉
怀着美梦却可以看见
摸索颠倒的一瞬间
所有的怀念隐藏在相似的日子里
心里的蜘蛛模仿人类张灯结彩
携带乐器的游民也无法表达
这对望的方式
接近古人
接近星空
捌
冬天是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当我的光曝在你身上
重逢就是一间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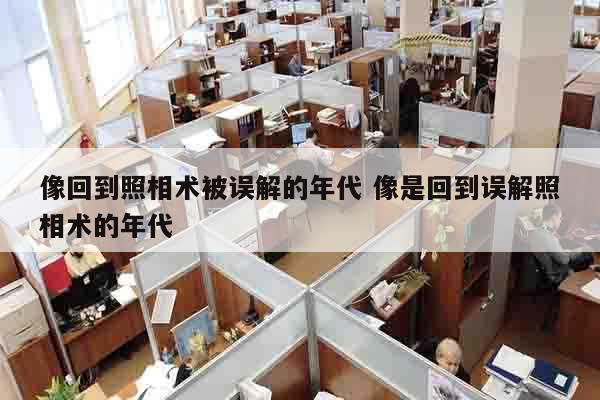
夏天,人的酶很固执灵魂的酶像荷花
文/摘自路边野餐
背着手
在亚热带的酒馆
门前吹风
晚了就坐下
看柔和的闪电
背着城市
亚热带季风的海岸
淹没还不醉的桥
不醉的建筑
用静默解酒
明天 阴
摄氏三到十二度
修雨刷片 带伞
在戒酒的意识里
徒然下车
走路到天晴
照旧打开
身体的衣柜
水分子穿越纤维
一
没有了音乐就退化耳朵
没有了戒律就灭掉烛火
像回到 误解照相术的年代
你摄取我的灵魂
没有了剃刀就封锁语言
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
二
山
是山的影子
狗
懒得进化
夏天
人的酶很固执
灵魂的酶像荷花
三
许多夜晚重叠
悄然形成黑暗
玫瑰吸收光芒
大地按捺清香
为了寻找你
我搬进鸟的眼睛
经常盯着路边的风
四
命运布光的手
为我支起了四十二架风车
源源不断的自然
宇宙来自于平衡
附近的星球来自于回声
沼泽来自于地面的失眠
褶皱来自于海
冰来自于酒
通往岁月楼层的应急灯
通往我写诗的石峰
一定有人离开了会回来
腾空的竹篮装满爱
一定有某种破碎像泥土
某个谷底像手一样摊开
五
今天的太阳
像瘫痪的卡车
沉重的运走 整个下午
白醋 春梦 野柚子
把会议揣进手掌的血管里
手电的光透过掌背
仿佛看见跌入云端的海豚
六
所有的转折隐藏在密集的鸟群中
天空与海洋无法察觉
怀着美梦却可以看见
摸索颠倒的一瞬间
所有的怀念隐藏在相似的日子里
心里的蜘蛛模仿人类张灯结彩
携带乐器的游民也无法传达
这对望的方式接近古人
接近星空
七
冬天是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当我的光曝在你身上
重逢就是一间暗示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和他老婆是在舞厅里认识的。
后来他们结婚,结在一个小房子里面。
小房子边边有一个瀑布,瀑布声音蛮大。
他们在家只跳舞,不讲话,因为讲话也听不到
《地球最后的夜晚》,可以不懂,但必须体验。(深文)
2018,12,31日晚.
糟糕了,趁着寒风走了好远才来看这场电影,现在却发现近视的我没带眼睛,电影的字幕好像被打了高斯模糊,人物脸庞好像用了水雾滤镜。
影片开始了七八分钟,我的思绪踯躅了一会。拿着啤酒跑到了第一排的空位,这时后面已有观众拿起手机以解沉闷,我猜想也有几对情侣趁着黑色亲吻,抚摸。因为这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人们习惯陪伴跨年寻找仪式感。
在说电影之前,我需要说说毕赣。他写诗,是一个现代诗人,而我觉得他的电影其实也是一首现代诗。
我记得网上一直流传着一段网红诗句,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许多人不知道它的作者是毕赣。
“ 许多夜晚重叠,悄然形成黑暗玫瑰吸收光芒,大地按捺倾向,为了寻找你,我搬进鸟的眼睛,经常盯着路过的风”
毕赣的其他诗歌,欣赏一下。
一.
“ 没有了音乐就退化耳朵
没有了戒律就灭掉烛火
像回到误解照相术的年代
你摄取我的灵魂
没有了剃刀就封锁语言
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
二.
“山
是山的影子
狗
懒得进化
夏天
人的酶很固执
灵魂的酶像荷花”
三
“今天的太阳
像瘫痪的卡车
沉重地运走整个下午
白醋春梦野柚子
把回忆揣进手掌的血管里
手电的光透过掌背
仿佛看见跌入云端的海豚”
这里只是选了三首。
我不知道你在读这些诗的时候时什么感受?
天性让你的理智在读东西时候都渴望捕捉它的逻辑,理清楚它们在讲什么。但是,这些诗歌以及很多现在的现代诗,读完了虽然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击力或美感,但另一方面,可能你就是不知道它们到底在讲什么。
一个故事?一种哲理?还是一种斗折蛇行的情感?
读者可能真的弄不清楚这些。这好似一个一个的意想的重叠与跳跃,哪有什么逻辑性?
同理可得,观众也这样。 因为毕赣的电影就是诗 。
那你可能会问,既然读诗,很难捕捉它们之间的逻辑,搞不清楚它们到底在讲的什么,说的什么。但为什么会有那种莫名的美感?
这里我想搬入一个词“同理心”。人对人不仅会有同理心。而且对物也是如此。
我们天生就对某些事情抱有某些情感。绝大数人看到蛇、蝎子会感觉到惊悚害怕,男生看到乳房就会觉得温暖与亲近,再比如人与很多动物天生就喜欢柔软与抚摸等等。以上所提的是我们刻画在我们基因里的固定情感认知。还有很多事物印象是在逐步成长过程中建立的,因为玩耍,因为经历,我们会亲近自然,喜欢鲜花,小狗等等,当然我们也会蛆就会觉得恶心,看到脓疮也会渗人,看到那些粗鄙的人也会觉得要避而远之。
也就是,我们的情感是与外面的物体相连接的。外界的实体可以激起我们的情绪反应,那可反证,我们也可以把我的情绪具象化,比如我们写作文惯用的比喻拟人手法。我爱你,我不会直接说我爱你,我会说“开门郞不至,出门采红莲”,我想你我也不会直接说我想你,而会说:“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红莲,骰子都是情绪的借景抒情物。
所以在我们心中有一家钢琴,各种意想若代表的情绪就是一个琴键。当你说“凌霄花”“夜莺”“险峰”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会弹起关于它的情感。
最经典不过“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而现代诗歌也是这样,各种具象化的意像就像一直钢琴家,弹奏一段音乐。潮湿的石头”“抱着盒子的姑娘”等等,导致了“悲伤”“忧郁”“小幸运”等等各种情绪在你心里逐级跳动,就像一种关于情绪的音符,do、re、mi、fa、sol、do~ mi..... 意像的跳跃让情绪搏动,感受就脱然而出。
其实就跟老师让我们评析古诗的修辞手法一样,只不过现代诗更不讲究前后顺接的逻辑性。
现在回到毕赣的电影《路边野餐》与《地球最后的夜晚》,很多人都说看不懂。主要因为我们的习惯认为电影就是要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哲理,或者一段沉重婉转的情感。我们总拿试着去理解它。但是如果我们抛弃这种看法,不要尝试着去理解它。
完全让电影的意像敲动我们心中的钢琴,让他弹奏一段独特的体验。这时候你就会体会到接连不断的意想带给你的体验。
如同欣赏一段纯音乐一样。不要把理性代入到音乐中,也不要去寻找固有的逻辑,只是体验。
这是我眼里毕赣的电影的魅力之处。很多人说看完毕赣的电影,明明不知道讲的啥,但还是会有不明觉厉的感觉。这就是因为电影给你营造了一种氛围,它给予观众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
光是明白这一点还不行,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还必须知道如何把一个接一个的意像链接起来,放在一个地方,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而毕赣用了一种极度巧妙且特殊的镜头完美地把它们表现了出来。
首先,毕赣用了很多第一视角画面。这种画面年轻人肯定很熟悉!因为电影用的就是吃鸡等第一系列游戏的第一视角画面 ,一个要去哪,要怎么样,要做些什么事情。 在加上前面2D的平叙,突然切换到3D的梦境, 观众好像觉得你就是在跟着个人走,跟着这个人去体验一些事情,一场梦境。
再者,就是电影饱受争议的长镜头。李诞说:“这部电影好像在拍的时候开了机就忘记关掉了”,确实这这样,《路边野餐》用了45分钟的长镜头,而《地球最后的夜晚》更过分,用了六十分的长镜头。 换句话,也就是你跟在一个人屁股后面整整走了一个钟头 。这种表现是方式是电影前所未有的。但是毕赣导演下的长镜头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画面,而是一直在讲述,反而形成了一种 重章叠沓 的感觉。
电影的长镜头总是跟着一个人再走,但是走着走着人物主体突然拐进去了一个小屋子或者别的小路,但这个镜头还在走,镜头里面路过了打桌球的青年,飘过了台阶,又遇见了一头驮着一袋苹果的马,但又突然在下个转角处,主人公又正好出现,正好接住,继续往前走。这种长镜头带给人们是无可匹敌的真实感。好像一首歌的副歌唱完,但音乐没停,在某个节拍又响起人声,继续演唱,如此完整和谐。
看他的电影我会想起小说《情人》里面的描写手法。
简在中国男人的屋子里与他度过了17岁的初夜,屋内生殖器的声音,女人的呻吟,床的晃动,床边的窗户,窗户外的街道,大街上中国菜的味道,吃饭的嘈杂的人声,远处的大海...笔触由近到远,再由外面的一切回到这一张床。 中间好像没有隔断,好像他们都是一体的,绵延不断的和谐。
第一人称视角+3D景深体验+永不停止的巨长镜头=如梦境般真实的体验。所以看毕赣的电影,你应该带着全然的体验过去。
以上是梳理的个人的关于电影的看法。
总体来说,就是如诗般的意想与独特的观影体验。但是很多观众为了寻电影的逻辑与意义而忽视了这些,觉得作者实在是无病呻吟,娇柔做作 。
接着,你说你这个电影是毫无逻辑的吗?这肯定的是错误。
毕赣在十三邀的时候说:“我拍电影,我不会把它直接表达出来,我会用一种比喻的形式表达出来。你看不懂也罢。我拍电影也不是为了让你看的。”
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毕赣电影充满了玄虚与意像。
你看他的电影,首先得知道他是一位诗人。
你看他的电影,首先你得喜欢读诗。
一个诗人在写诗的时候时全然没有逻辑的吗?肯定不是。
有一个例子。有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说,你想写诗吗?
学生说想。老师说:“好,那你现在闭上你眼睛。看看你的脑袋会想什么”。
“我想到了大树,草地,我的爸爸”
老师说:“不要停接着想”
“小时候追着跑的钢圈,摔倒的伤口,还有一直黄色的狗...”
“好,睁开眼睛,现在把它们运用文字描写出来,再加以一些韵律与节奏,就成诗了。”
心中这些画面的跳跃也暗含着一种感性链接关系。它可能源自个人记忆 ,心理症结或者别的因素。
那些看不懂的诗歌其实也是有逻辑的,只不过这种逻辑可能只有作者或者少数人知道。
说实话,毕赣想要表达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深沉地哲理或者一个令人惊掉下巴的故事,他要表达或许仅仅是他的某种情绪,他的残缺的家庭梦影,或者是他压抑在心底的某种渴望与重建。
毕赣利用诗的工具与摄像机的镜头把这种梦境与迷思具象化了。
电影中处处都是意像的重叠与梦的混乱。
万绮雯和罗紘武之间野柚子的赌约,房间旁漏水的也柚子树,那个歌厅的名字也叫野柚子。万绮雯给左宏元的人叫老A,后来他被左宏元杀掉。“白猫”的尸体在矿洞被发现,现场遗落了一张黑桃A的扑克牌。万绮雯告诉罗宏武怀孕时罗紘无说他可以教孩子打乒乓球,后来在那个山洞中那个带着鬼面具的孩子却要求和他打乒乓球.. ..
这些野柚子,黑桃A,白猫,绿皮书,乒乓球等等...这些意像后面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对过去的纠结与遗梦。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详细给我们阐述了人是怎样过通过梦去处理自己压抑的情思或者未满足的缺陷。在他的各种临床案例给我展示梦的复杂与神秘性,一个女生经常梦见蛇可能证明着她对阴茎的某些情感,从高处坠落的梦可能暗含着着现实中的抛弃,梦里的马可能象征你的母亲...... 本我一直在被超我压抑着,那些原始冲动、情思、欲望沉浸在我们深不见底的心海,因为他们害怕道德标准、世俗眼光的审判的猎枪。只有在梦中,它们才敢把自己精心伪装起来,骗过城墙门禁的检查,出来透口气,跳一支舞,然后在天亮人醒之前赶紧继续躲避起来。
这样你就可以带这一种重新的眼光去审视毕赣的电影中的意像了 。它关于梦,关于诗,关于艺术的具象化,关于最深层的压抑与人性...
梦,是个太神奇的东西了。
科学已经证明梦与人压抑的欲望,与白天的学习记忆,与脑电波的摩擦放电有关。但我们对梦的认知只是冰山一角。还有一些是未被证实的。
当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我的脑波是在5Hz以下,而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睡眠可以与地球磁场发生共振,也就是当深度睡眠的时候,人与某些东西是不是就统一了呢?爱因斯坦证明时间空间的不存在。多数人都知道梦会把时间与空间扭曲。
在毕赣的电影中关于时间扭曲的象征物随处可见,《路边野餐》里面的火车,《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表。
梦里与过去与未来,现在还是一个谜 。
荣格的关于梦的集体无意识中阿尼玛、阿尼姆斯、莎乐美印象是否真的存在?
影片《地球最后夜晚》中男主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母亲就职的歌厅后,紧接着就是问出“她多少岁”此时,在电影的画面里,我们已经分不清哪个是母亲,哪个是情人,可能她们是同一个人,也可能是俄狄浦斯情节的表现。
这不就是典型的最心底潜抑在梦中的表达。
而你要知道毕赣导演从小父母离异。而电影拍摄的所有地点也是毕赣的老家,凯里。(这里并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回到电影,罗紘武拿着武器在问清楚那个类似母亲形象的女人要私奔的原因后,他释然了,然后用枪逼迫着那个男人带走母亲。这其实是罗紘武的一种自我解释。母亲说:“我吃了太多苦,而他那里的蜂蜜很甜”。 因为母亲抛弃了他,他一直从小抑郁于心,好了,现在知道母亲要走的原因了。所以我不再恨她,我也不再对自己疑惑了。
心理医生在治疗一些在某些方面有心理阴影的病人的时候,会采用催眠手法。病人可能因为小时候的一次不好的经历而有一些不正常恐惧。当他们被催眠后,催眠师让他们回忆最初的那次经历,而这些经历在现实生活中是被病人一直压抑着的,比如一个孩子可能因为母亲的某次抛弃而缺乏安全感,后来经过大面积移情而渗透到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催眠中,医生引导病人回到那个根源,会重塑或者转移那段经历,播下爱的种子,从根底上修正认知。
影片中这个片段其实和上述的那个催眠原理一样。从认知上,尽管真相可能不是这样,但是这样就是可以把自己从无期徒役中解放出来。
影片中到处相互联系的意像是这些矛盾 间接表达 或者 自我化解 。
当罗紘武要离开那个小男孩时,他问:“门不关,不怕有人偷东西吗?”少年答“除了你谁还会来?” 这个打乒乓球的少年是主人公那个被打掉的孩子的自我解离。
但扒去层层喻体与掩饰之后,这个电影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
他只是一个人的故事。毕赣只是把一个平常个人的压抑下的梦境展示了出来,它是架构在时空的扭曲与永恒之上人的情感的轮回与裂变。
我想起来张爱玲《金锁记》中的一句话: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毕赣把压抑的梦出来,因为梦境善于伪装,所以电影也很难懂。
如果能弄清楚情节之间、意像之间的关系,那就明白电影的表述了。但是这些东西太隐匿了,太个人化了,大多数人都发觉不到。
不过,如果不懂也没关系,那就安安静静带着朦胧的理解地去体验它吧。那些不懂的意像也会在你心中的钢琴上弹奏出独特的体验。
最后,把毕赣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我的电影就像一场大雨,但你们不要带伞”
转载//毕赣《路边野餐》现代诗
壹
背着手
在亚热带的酒馆
门前吹风
晚了就坐下
看柔和的闪电
背着城市
亚热带季风的河岸
淹没还不醉的桥
不醉的建筑
用静默解酒
明天 阴
摄氏三到十二度
修雨刷片 带伞
在戒酒的意识里
徒然下车
走路到天晴
照旧打开
身体的衣柜
水分子穿越纤维
贰
没有了音乐就退化耳朵
没有了戒律就灭掉烛火
像回到 误解照相术的年代
你摄取我的灵魂
没有了剃刀就封锁语言
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
叁
山
是山的影子
狗
懒得进化
夏天
人的酶很固执
灵魂的酶像荷花
肆
许多夜晚重叠
悄然形成黑暗
玫瑰吸收光芒
大地按捺清香
为了寻找你
我搬进鸟的眼睛
经常盯着路过的风
伍
命运布光的手
为我支起了四十二架风车
源源不断的自然
宇宙来自于平衡
附近的星球来自于回声
沼泽来自于地面的失眠
褶皱来自于海
冰来自于酒
通往岁月楼层的应急灯
通往我写诗的石缝
一定有人离开了会回来
腾空的竹篮装满爱
一定有某种破碎像泥土
某个谷底像手一样摊开
陆
今天的太阳
像瘫痪的卡车
沉重地运走 整个下午
白醋 春梦 野柚子
把回忆揣进手掌的血管里
手电的光透过掌背
仿佛看见跌入云端的海豚
柒
所有的转折隐藏在密集的鸟群中
天空与海洋都无法察觉
怀着美梦却可以看见
摸索颠倒的一瞬间
所有的怀念隐藏在相似的日子里
心里的蜘蛛模仿人类张灯结彩
携带乐器的游民也无法表达
这对望的方式
接近古人
接近星空
捌
冬天是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当我的光曝在你身上
重逢就是一间暗室
《路边野餐》:静默成诗,鬼气浪漫
一个曾经熟悉或去过的地方,当其以电影的方式出现时,那刻所见所感是与众不同的。电影因人而异的缘故,有了作品之外的属性,弥漫出些许回忆的气息。其实《路边野餐》更适合叫原本的名字——《惶然录》,里面的人物看似早已随遇而安,然现实和梦境都氤氲着不安的氛围,交错出总带着些阴郁的往昔。
若没有在贵州生活过多年,若不是心里也有往事的伤,《路边野餐》之于观众而言,不过是一部看完只觉懵懂而迷惑的小众电影,甚至会觉得看了一部DV拍的纪录片。说到以贵州为背景的电影,上一部记忆深刻的是十年前的《青红》,犹如旁观父母那代人的仓促青春。这才是电影精分的魅力,能让人找到被遗忘的情愫。
一、 凯里:现在心不可得
“凯里东接台江雷山两县,南临麻江丹寨两县,西部福泉县,北接黄平县,地理位置在东经107.40.58-108.12.9,东西最长跨度51.76公里,南北最长度44.3公里……”后面洋洋过河时背的导游词中,凯里再次以书面文字的形式登场。往往会看城市简介的,不是在此生活多年的人,而是充满好奇心的客。
故事从停电的凯里诊所开始,穿白大褂的陈升却是病人。在空旷的露台上,老医生望着入夜的凯里,唠叨几句服药的医嘱,嫌弃酒鬼的狗又跑过来。天无三日晴,阴沉而潮湿,给影片罩上自来旧的滤镜,如同多次出现发霉的旧墙、滴答漏水的屋内,还有多云不放晴的天空。占了过半篇幅的凯里,是陈升生活的现在,有他的工作和亲友,还有他的困顿与无奈。
从防空洞里走出来,陈升看上去很孤单,实际上也很孤独。人到中年,孑然一身,妻子病逝,母亲也去世了,弟弟与他不亲近,就剩下侄子卫卫算个慰藉。这样的男人,平凡如任意的路人甲,乍一看没什么特别,却爱写抽象的诗。写诗还出了本集子,他怕也多少有些故事,毕竟诗人是罕见的身份,除了言之无物的回车键。
背着城市
亚热带季风的河岸
淹没还不醉的桥
不醉的建筑
用静默解酒
贵州没有平原,哪怕大些的城市,也多有陡坡还连着山。而这里的山,不比别的地方,更像拔高的野地,无序混杂长着荆棘和灌木,在怪石间又种着玉米高粱等庄稼。近看远看都是杂乱无章的野地,外行人也难辨哪些是人为种的,哪些是自行生长的,山头倒像是被剃坏的短发,东一块长西一块秃。我视之为野蛮生长,一个“野”字颇有个性。
地方其实和人一样,都有各自的脾气和性格。贵州多高山且险峻,河流瀑布都湍急,山洞和防空洞也多,随处可见的野地风格,生出些许与众不同的“鬼气”。我所谓的鬼气,与鬼神志怪无关,而是形容黔地的神秘,仿有灵力去引人探寻。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哪怕看着毫不起眼,必有些内里的曲折,就像多重身份的陈升。
当诗人时,他是细腻的。当医生时,他是耐心的。当丈夫时,他是深情的。当朋友时,他是仗义的。当哥哥时,他是忍让的,当伯父时,他是慈爱的。只有当儿子时,他是逃避的。他后来的种种,究其根本,源于孤独的童年,甚至有被抛弃的类似感觉。于是,他才会特别珍惜情感,因为最需要时缺失过。
没有了音乐就退化耳朵
没有了戒律就灭掉烛火
像回到 误解照相术的年代
你摄取我的灵魂
没有了剃刀就封锁语言
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
说到这里,陈升的人设都是趋于完美的。而现在都是当下的表象,过去的黑历史仍会现身。原来,年轻时陈升跟过大哥混过社会,后因替大哥出头断人手指被判刑。没心如行尸走肉,九年牢狱之灾,陈升就此失去了母亲和妻子,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
之后日子里的陈升,好好地活着,却没了盼头。直到得知侄子被卖,陈升对弟弟老歪怒了,拿母亲留下的房子作交换,以换取小卫卫日后的安稳,也从而踏上了找寻的路途。这时起,小卫卫成了陈升的期望。人要想踏实地活,总得找些念想,也好义无反顾走下去。
在这里的现在,每个人都不快乐,每个人又无能为力,只有照着习惯的轨迹走。整个城市仿佛笼罩在下雨前的闷热中,人们心中都有些憋屈的郁结,不闻不问地耽搁久了,一旦动手整理起来,就像老医生的旧箱子,一拿出来就散架了,放久了鞭炮也点不着。到处似乎都是无可奈何的错过,尽是于事无补的遗憾。
二、荡麦:未来心不可得
梦见母亲穿的绣花鞋,梦见蜡染布上的图案,梦见苗人吹奏的芦笙曲,陈升将这些挥之不去的梦境,都归结为快拆迁的老房风水。片子里数次提到梦的内容,老医生梦到车祸死去的儿子、花和尚梦到儿子想要块表,还有陈升在火车上梦到的荡麦。梦就是一个幽灵,趁着意识睡着了,从心的黑洞飘出来放风。
弗洛伊德曾解释说,“睡眠的时候,心灵面对外界的刺激,要么不予理睬,要么采用梦去否认它的存在,或者“编织栩栩如生的谎言",尽可能地延续睡眠。因此,我们可以把'睡眠的欲望'也看成是梦的动机之一,每一个梦都是这种欲望的满足。”于是,梦承载了众人无法释怀的过往与失去。湟然不可得,初心方成梦。
一定有人离开了会回来
腾空的竹篮装满爱
一定有某种破碎像泥土
某个谷底像手一样摊开
说到荡麦的段落,有人着迷于四十多分钟的长镜头,有人在争论究竟是梦还是真实,还有人在纠结于时空的交叠。就像关于野人的说法,众说纷纭难下定论。而我的第一感觉是将荡麦当做臆想中的一场告别,也是陈升对自己的一种开解。
从不唱歌的陈升主动当众唱了首《小茉莉》,开摩托的小年轻爱吃粉爱画钟表也叫卫卫,开理发店的少妇长得和亡妻很像也想看海,疯癫的酒鬼竟然成了司机但仍爱喝酒,这些在凯里都熟悉的面孔好似有些不对劲。这种不对劲却是圆满的,梦中没有遗憾的立足之地,陈升仿佛又见到了亡妻张夕,为她唱歌还描述大海和海豚,卫卫长成了大人有了喜欢的姑娘,连只会在废车里闹腾的酒鬼都正常了。
巧合得不可思议,就可能是个骗局。陈升送出磁带时,说是李泰祥的《告别》。我突然明白过来,在荡麦发生的一切,都是陈升借着梦说再见。跟过去的往事告别,跟过去的自己告别,跟过去的妻子告别,跟过去的母亲告别,陈升自导自演着跟过去和解。只有真送走了过去,陈升才能继续未来的生活。
白醋春梦 野柚子
把回忆揣进手掌的血管里
手电的光透过掌背
仿佛看见跌入云端的海豚
唯一的新面孔是洋洋,她是过去无关的人物,她是即将要离开荡麦的,她就像是属于未来的存在。在整部影片里,只有洋洋的裙子是鲜艳的亮色,回忆里的张夕虽穿着红色连衣裙,却是偏暗沉的深红,远不如洋洋的柠檬黄来得跳脱,点缀了所有的暗沉与压抑。这样的黄色,代表着希望、光明和快乐。
我很喜欢洋洋去坐船的片段,兜了个看似无意义的圈,可是你还在我身边等着。沿着屋旁的石阶走到河边,上船开始背本上的导游词,卡壳时听到大卫卫在岸上大声提醒。洋洋下船买了个风车,可风车被等着的大卫卫抢走。洋洋听到火车开过的声音,大卫卫把风车弄坏了。两人一起走过河上的吊桥,大卫卫提出陪她去凯里,洋洋沉默却没有拒绝。又回到了原来的路径,洋洋过河其实什么也没做,甚至没必要坐船过去。可是,回来后洋洋的心已经有了决定,关于和大卫卫的关系,后来给摩托车上绑红绳是接受。
大卫卫虽有些小滑头,却还是信守承诺的人,他一边载着陈升去坐船,一边嘱咐对付野人的方法。果不其然,大卫卫给陈升的胳膊上绑了木棍,那个样子实在滑稽而可笑。等船时,陈升拆掉了木棍,因为他已经不再惧怕所谓的野人,也终于松掉了心头的捆绑。野人是回忆里的死结,因为曾经不敢面对,所以总没勇气解开。
三、镇远:过去心不可得
终于来到了颇有渊源的镇远,也终于见到了吹芦笙的苗人,原来老医生念念不忘的林爱人就是芦笙师傅。陈升找了一路的苗人,吹芦笙是给林爱人送葬。老医生没有来或许是对的,分开了半生的旧时恋人,若见他病重是心焦,未履行承诺也心焦,知道死讯更是心伤。无声的牵挂终究败给了时间,再多的思念却终究挽不回重逢。
在片中,镇远与人物的过去,有着剪不断的纠葛。陈升在这里度过了孤独的童年,而他的母亲对这里有着深深的歉疚,老医生知道曾经的恋人一直在这里生活,花和尚选择在这里开间钟表店抚慰丧子之痛,以及埋葬曾经混社会当大哥的过往。镇远就像《花样年华》结尾里吴哥窟的树洞,装着许多人的旧时光与秘密,静静地望着有人来有人走有人停。
所有的转折隐藏在密集的鸟群中
天空与海洋都无法察觉
怀着美梦却可以看见
摸索颠倒的一瞬间
关于镇远的戏份,只有最后十来分钟。于大多数人而言,现在是冗长的,未来是飘渺的,过去是零散的。所有当下与以后的脉络,都来自那些不连贯的过去,如同奔涌的江河源于不起眼的细流。长久以来对爱的渴望与缺失,都是从陈升在镇远的日子开始,然而他的童年以及和母亲的心结,始终都是透过旁人的口说出的,他自己似乎并不愿过多提及。
许多年后,陈升为找侄子再次回到镇远,既像重温记忆,又像重复命运。一直以来,陈升对小卫卫的照顾,几次提出让侄子跟自己过,除了亲缘关系和母亲遗愿,还因为他的困境像极了儿时的自己。被远离亲人,被独自生活,不过是体面些的抛弃。
岁月和失去是至烈的侵蚀剂,曾经的江湖大哥如拔牙去爪的老虎,花和尚以老者的絮叨不愿让陈升接走小卫卫,他脆弱地将孩子当作亲情的替补。老旧的电风扇,和各式的钟表,有所指代地出现了,循环往复总不顺畅,修了又修好好坏坏,过去不可得,岁月亦不可追,上了年纪更易陷入记忆的怪圈。若说陈升看小卫卫像自己,花和尚又何尝不是看陈升像自己?尝过后悔滋味的人,才更懂得珍惜眼前。
冬天是十一月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当我的光曝在你身上
重逢就是一间暗室
终究没能狠下心,陈升留下了几颗纽扣,和周一的最后期限,躲在暗处用望远镜,远远看了眼小卫卫便走了。小卫卫后来究竟有没被陈升接回去?想到未言明的以后,感觉就像读沈从文的《边城》,揣测走了的翠翠是否会回来。
长大后的小卫卫,会成为大卫卫、陈升、老歪或是花和尚,其实就取决于他的境遇,以及他面对的态度。陈升和老歪这对兄弟,家里都挂着旋转彩灯,舞厅的元素出现在此,带着些超现实风格的反差。一个挂在嘈杂明亮的阳台,一个挂在昏暗潮湿的屋里,就像一个选择努力生活,而一个选择浑浑噩噩。不同的人生,怪不得命,却怨得了己。
车后的隧道口变得越来越小,前方的光亮却越来越宽阔,陈升回去时又打了个盹,闭眼的时候对向火车上有倒走的钟。小卫卫看到了,却没马上接走,陈升至少算是放心的。林爱人找到了,却只有送葬曲,陈升也算是忠人之事。而荡麦的一游,梦也罢,幻也好,陈升终于是有所收获,有些重逢的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治愈。
灌热水瓶时闷闷的声音、木头书桌上的小盆文竹、窗户可打开的绿皮火车、蓝布蜡染和黑衣苗人、随处可见野地山头里的苞米、喧哗的瀑布和黢黑的山洞……尽是遥远的念想碎片,度过了最初童年的地方,哪怕离开许多年未归,是好是伤早已挥之不去。
《金刚经》中如是说,“过去之心不可得,现在之心不可得,未来之心不可得。”这部电影之于我,如同荡麦之于陈升,在不为人知的时空梦了一场,醒来该忘的忘该放的放,然后逐渐成为更坦诚的自己。既知不可得,或能少憾事。
片名的英译是Kaili Blues,与诗相配的蓝调,自带忧郁的情绪。被汞矿染蓝的水塘,像海却不可能会有海豚,因是重金属超标的污染。还有陈升说和张夕结婚时,住在瀑布旁的小房子里,两人在家只跳舞不说话,因为说了也听不见。只出现在台词里的景象,在静默的时光中回顾,幻想出来竟觉浪漫,沾染着返潮空气中的鬼气,写成了光怪陆离的诗句。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